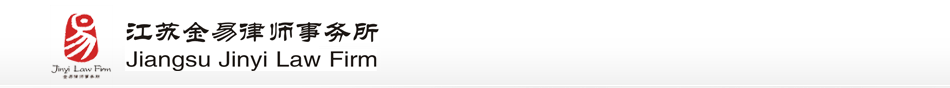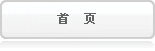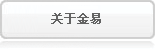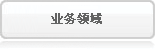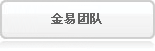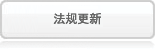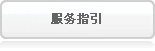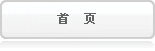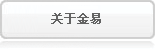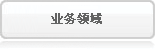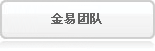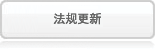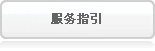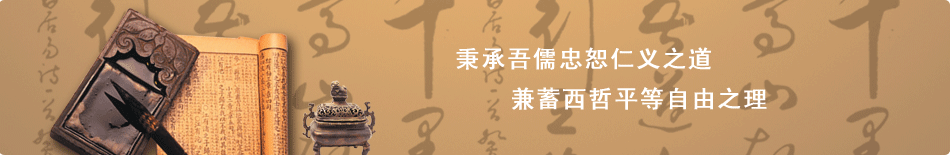律师的二种职业
伦敦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法律服务业的中心之一。其律师业的发达既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又享有强大的现代竞争优势。说起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一方面,英国的律师业已有七百年的历史,这得益于英国近千年历史中对法律和规则的尊崇。在格雷律师院的院子里,还保留着律师拴马的桩子,你可以想像当年律师牵着马,穿着袍,当事人把钱放入律师袍后面的帽子里的情形;另一方面,大英帝国的扩张也带来了治外法权的扩张,历史上英国的枢密院享有对英联邦国家的司法终审权。在香港回归并设立香港终审法院前,上诉案件往往一杆子就捅到了伦敦,大家对八、九十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中的这些场景或许还留有印象。但是,随着各英联邦国家司法的纷纷独立,伦敦的法院不再有以往的荣耀,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伦敦律师业的发达。世界第一大所高伟绅的总部就在伦敦,这个在众多世界顶级银行大楼之间拥有一座现代化律师楼的律所,麾下律师数千人,年收入近10亿英磅。年利达、富而德等挤入世界十强的律所总部都在伦敦,当然它们的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
在英国,出庭律师(诉讼律师,英文名为Barristers,故又称为巴律师,在香港称为大律师)与事务律师(非诉律师,英文名为solicitors,故又称为沙律师)是二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出庭律师可以理解为个体户,专事出庭诉讼,有时也为客户和其他律师出具法律意见。虽聚集于伦敦四大律师院的若干个出庭律师事务所,但是除公摊费用外,基本各自独立核算,多收多得,因此,出庭律师事务所的作用仅类似于俱乐部。但是,松散的组织形式丝毫不影响这些大律师们的职业素养、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人们见到他们的往往是白天头戴假发,身穿法袍,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激越雄辩的一面,而很少看到深夜他们在办公室里阅读成箱的案卷,在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浩瀚的案例报告中检索判例的一面。
四大律师院(分别为Gray’s Inn, Lincoln’s Inn, Inner Temple, Middle Temple)的建筑保持着数百年前的风格,深灰色的、暗红色的墙壁,白色的窗檩,长长的组成一个个院落,中间围着方形绿地,显得安详静谧。格雷、林肯等律师院二战期间均遭到了轰炸破坏,但是他们没有借此进行“改建”、“扩建”,而是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有些墙体上留下的累累弹孔索性原封不动地保留。早晨的院子里,律师们穿着风衣,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有熟识的见面,相互轻声打个招呼,有秘书将装着一箱箱文件的小车推出院子,那是有律师要到法院出庭了。
而事务律师的组织形式比较现代,事务所采用有限合伙制,实行公司化管理,规模小到数十名律师,大至数千名律师,除了诉讼案件外,主要从事金融证券、公司并购、建设工程、资产融资等诸多非诉讼领域的法律事务。当然他们的大楼比出庭律师的气派和现代得多了。一些国际律所简直是“法律工厂”,有几千人在一个大楼里制造成堆的文件,分别送到客户或者法官手里,以换取客户的支票。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这些事务所愈来愈重视来自中国的客户。例如,一家伦敦律所的资产金融部就从中国的一家航空公司身上赚足了钱,他们为这家航空公司购买新飞机的融资安排提供法律服务。
当然,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又是密不可分的,在诉讼案件中,出庭律师不能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只能接受事务律师的委托,也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律师费,只能由事务律师支付。一个案件的成功,少不了出庭律师和非诉律师的密切配合。好的出庭大律师有钱都不一定请得到,而初出茅庐的律师面临着案源的很大压力,在拼命工作之余,偶尔请事务律师喝杯啤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高昂的律师费用
伦敦的律师收费均是以小时计算,不管你请的是诉讼律师还是事务律师。如果你想请好的律师,必须付出高昂的价钱。如果你案件的标的很小,而你的收入状况和案件的性质又够不上法律援助,那么你最好选择采用别的方法解决纠纷,否则一场官司下来,你付出的律师费可能是案件价值的数倍。当然,在英美法的诉讼体制下,如果你案件胜诉了,并且在证据批露等审理程序方面比较合作,一般法院会判对方支付你的律师费用。当然,你输了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承担对方的律师费,所以一些财大气粗的当事人常用的诉讼策略就是穷尽一切程序上的权利,将诉讼时间延长延长再延长,直至对方因财力问题而投降,被迫接受和解方案。因此打官司不仅仅是法律的较量,也是双方当事人经济实力和勇气的较量。
伦敦从来不缺乏好的律师,只要你愿意付好的价钱。最优秀的律师将会被封上QC(Queen’s Counsel,即王座顾问)的称号,惟少数杰出的法律人士方可获此殊荣,全英格兰仅一千二百人左右,而全英格兰的律师有十一万人之多(与我国的全国律师人数相当)。王座顾问中有四五百人从事执业律师,其他的则从事法官、教师、政府官员等职。而一名QC参加庭审往往会有一、二名出庭律师作为助理同时出庭,而出庭律师又有事务律师坐在后排协助,因此,当事人聘请了一名QC做其律师,就意味着他除了要支付这位王座顾问高额的律师费外,还得承担数名其他律师的律师费。当一场官司旷日持久时,当事人接到律所一张张的帐单,那种感觉叫做“玩的就是心跳”。
我的导师霍奇•麦立克先生是个年轻的QC,他具有一半的伊朗血统,是个穆斯林,一个与犹太人水火不容的民族,但是,他的著述《证据批露》一书却是在办公室隔壁的一位犹太律师的协助下共同完成,在这个事务所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麦立克先生主要法律领域为金融、保险、信托,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是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正是因为QC的律师费昂贵,有会议的话,金融监管局的人情愿到事务所来开,这样可以省去律师在途时间的计费。有一个案件,事关金融监管局对一家保险公司的违规处罚,金融监管局认定这家公司将高风险的产品出售给靠养老金生活的一般客户却未尽风险告知义务,决定罚款110万元英磅。这家公司也是世界排名靠前的保险公司之一,“处罚事小,名节事大,”毫不含糊,请了一流的律师(当然也是QC)打官司。按照程序,先是到专门的金融服务监管仲裁庭仲裁。裁决结果出来,认定违规属实,罚款金额则变更为57.5万元英磅,律师费用双方各自承担。霍奇告诉我,到这时候这家保险公司的律师费支出已达500万英磅。
在如此高昂的律师费体系下,英国虽然也有法律援助制度,但是,援助经费往往是杯水车薪。民事案件中一般居民不够条件获取援助,一位英国出庭律师公会的官员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自己几年前有一桩合伙的纠纷,涉及十来万英磅,启动诉讼程序后,由于审理进程似乎毫无止境,律师费却与日俱增,无奈最后放弃了诉讼。刑事案件的援助经费也是少得可怜,律师拿到的只往往只够车码费,辩护质量可想而知。看来,英国在法律援助问题上应当到中国来取取经。